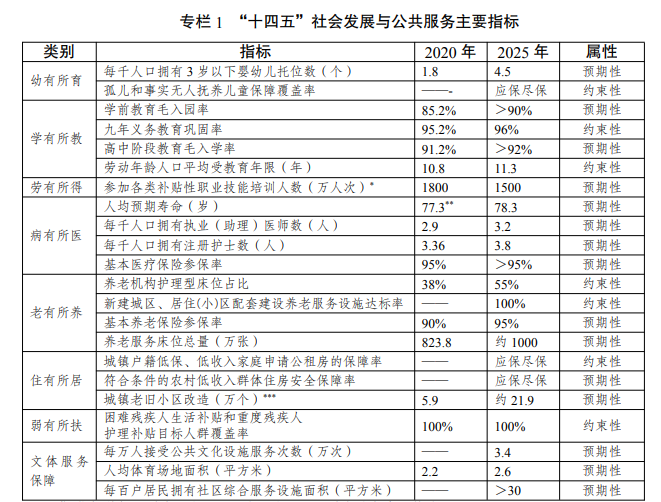赵红程操纵轮椅如臂使指,无比丝滑地驶过舞台上的斜坡:“瞧瞧这流畅的曲线,时尚的配色,顺滑的轮子,灵活的转向,再加上它时速25公里续航8小时的电动车头,真是绝了。该怎么形容它有多猛呢——启停急了,你会晕车。没有人会不想要这样一台轮椅。”
改编自真人真事的话剧《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下月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独角戏此前已在上海演出,主角赵红程是一名为残障人士发声的视频博主,她以素人身份出演话剧,将在舞台上说出她的故事——适合公开讲述的故事和“难以启齿”的故事。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赵红程操纵轮椅如臂使指,无比丝滑地驶过舞台上的斜坡:“瞧瞧这流畅的曲线,时尚的配色,顺滑的轮子,灵活的转向,再加上它时速25公里续航8小时的电动车头,真是绝了。该怎么形容它有多猛呢——启停急了,你会晕车。没有人会不想要这样一台轮椅。”
我和身边的观众都发出“哇”的惊叹,真的有点儿羡慕。轮椅似乎不再是脆弱的标志,而是身体的某种延伸。我好像不是在看一个可以被归类为残障剧场的作品,而是在看一个赛博格剧场:轮椅是构建新身体结构的工具,既让残疾变得可见,又让残疾的身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表演。
在自传性独白剧场《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中,有许多这样的时刻,让观众因为面对一个难以简单定义和归类的真实个体,超越了对于残疾隐喻的符号化解读,而产生了同情和敬佩之外的复杂情绪,同时又不免悄悄怀疑:我的这种反应合适吗?得体吗?
在生活中被凝视在剧场中遭隐形
这是自小罹患脊髓灰质炎而无法行走的赵红程第一次在剧场表演,可能也是大多数观众第一次在剧场见到真实的残疾人登台。这就是残疾人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需要面对观众的凝视,正如剧作家、轮椅使用者约翰·贝鲁索所说,残疾人一直在舞台上,每次坐上公交车都是一个被观看的戏剧性时刻;另一方面,真实的残疾人却极少有机会出现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如果像欧文·戈夫曼所说,日常生活是一种表演,那么残疾人往往是以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戏剧化的方式来表演他们的身份的。
对赵红程来说,进入电梯就像一个怯场的演员硬着头皮登上一个互动式舞台:“每次走进电梯都像开盲盒,不知道今天老天又给我送来什么小惊喜。我一直很纳闷,好多日常生活里没人想问,或者没人好意思问的问题,怎么会在电梯这个封闭的小空间里,顺顺当当就能说出口了?”面对这些无知而傲慢的“观众”,她娴熟地提供预期的类型化角色:礼貌、风趣、乐观、随和。
而真实的残疾人在剧场中是隐形的,因为舞台不需要残疾的身体,只需要残疾的隐喻。在文学、修辞学和视觉传统中,残疾开启了阐释行为,其功能是表示差异——某种格格不入、需要纠正的东西。典型的残疾人物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执著的复仇者”,他要报复那些他认为应该对其残疾负责的人;“可爱的无辜者”,他是非残疾人的道德晴雨表;“滑稽的不幸者”,他的残疾引发了身体的喜剧性;“励志的战胜者”,克服缺陷而成为杰出人物,以及“怪胎”和“怪物”,引起人们恐惧的局外人。
明显的残疾身体很少占据戏剧舞台的中心,最著名的残疾角色可能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他的“畸形陋相”被理解为邪恶人格的表征,戏剧的结局以残疾身体的消亡宣告王国秩序的恢复。不仅如此,作为隐喻的残疾角色通常还是由非残疾人演员扮演的,甚至成为某种特殊演技的炫示——这意味着对残疾人的双重遮蔽与剥夺。
残疾,一种与不友好的世界互动的方式
在《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中,赵红程呈现的是摆脱了隐喻的真实个体。她没有扮演虚构的角色,敷演虚构的情节。编剧陈思安将赵红程的真实经历凝缩成一个特定情境:作为一个残疾人,如何在公开演讲中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因为它使赵红程同时成为主体和客体,成为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她写了两份演讲稿,一份是社会期待的版本:乐观、坚韧、励志;一份是私人的版本:逻辑混乱,政治不正确,甚至有粗口。
“无论讲哪一份,我都没有撒谎。然而无论只讲哪一份,我都在撒谎。”在不断追溯、设问和自我怀疑的过程中,赵红程讲到陌生人的凝视,讲到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讲到第一次穿裙子的感受,讲到深刻的不安全感。她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又保持距离地审视残疾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导演和舞台设计师赋予舞台一种灵活的动感,让观众感受到坐在轮椅上的是一具自我探索的、不安的、骚动的身体,因为太具体太丰富而难以归类、难以抽象。
对我来说,独白中最动人的部分是赵红程讲述她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去做了脊柱侧弯手术和腿部矫正手术,在病床上躺了109天,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只为了一丝能够站起来的渺茫希望。这个勇敢的决定背后是脆弱。她说:“那时,我固执地相信自己前25年人生所经历的种种限制、痛苦、不自由,都只是因为我无法站起来。只有站起来,我才能成为一个别人眼中完整的人!”手术后赵红程可以短暂地站立,但仍然无法摆脱轮椅。她说,她因此了却了执念。
这个执念或许并不是赵红程个人的,而是一种内化的规范性理想。而手术无助于改善赵红程的生活,或许也说明用医学模式看待残疾问题的失败。医学模式将残疾人视为“病人”——一种幼稚化、病态化和被剥夺权利的。那些无法治愈或无法康复到“合格”的病人往往被隔离在非残疾人的主流社会之外。讽刺的是,医学的进步并没有消除残疾,反而使残疾越来越多。因为更多的人得以从受伤和疾病中幸存下来,带着明显的缺陷生活。
与此相反,社会建构模式将残疾理解为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脱节。正如《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这个剧名所表达的,是轮椅使用者面前的楼梯或盲人面前的普通印刷文字造成了个人残疾,而不是身体缺陷本身。赵红程最后说:“残障,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但不再用看待病人的眼光看待我自己,是我可以改变的事情。”如果不把残疾看做是一种身体状况,而看做是一种与经常是不友好的世界互动的方式——是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这或许就是赵红程在剧中再三强调“看到我”的意义。
每个人都可能因不公和压迫而“残疾”
近年来国外以残疾为主题的剧场艺术(以及广义的表演)的发展,大多采用社会建构模式对残疾的理解,致力于解决残疾身体的文化边缘化和残疾人的隐形化。尤其是舞蹈和舞蹈剧场,如热罗姆·贝尔的作品中,受过专业训练的非残疾人舞者和残疾人舞者并列,代表着一种特殊训练和美学传统的舞者与代表着对这一传统挑战的身体特征的舞者并列,以此对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构建的审美规范提出质疑。和舞蹈剧场相比,在戏剧性的,或以语言为基础的剧场中,虽然已经有剧作家明确地要求其笔下的残疾角色必须由残疾人出演,但整体上仍然受限于一种排他性的、封闭的和同质化的身体类型。
对国内剧场而言,《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偶然:制作人沈璐珺因为髌骨骨折,在家休养的时候刷到了赵红程测评无障碍设施的视频,萌生了邀请这名网红博主演戏的念头。赵红程发现,临时受伤的人会更理直气壮地提出对无障碍设施的要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从健全到不健全的落差会开启新的视野,使原本习以为常的非残疾人的世界变得陌生,也使人意识到,残疾的身体只是人类形态的连续体中的某个点。
残疾研究学者伦纳德·戴维斯曾经提议使用“暂时健全人”,来强调正常不过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这个词使健全成为一个偶然的变量,因为所有人类的身体,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有限的、易变的,而且注定会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身体都必须接受有限和无能。虽然“我们都是残疾人”这样的宣言,听起来像不假思索的陈词滥调,然而事实就是,我们都有可能因各种不公正和压迫而残疾,我们都是非标准的。残疾即使不是一种普遍的身份主张,也可以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普遍视角。
就像舞台上的赵红程所说:“每个人一生最终的归途都是坐上轮椅,我也只不过是比其他人更早一点体验罢了。”
本版摄影/王犁